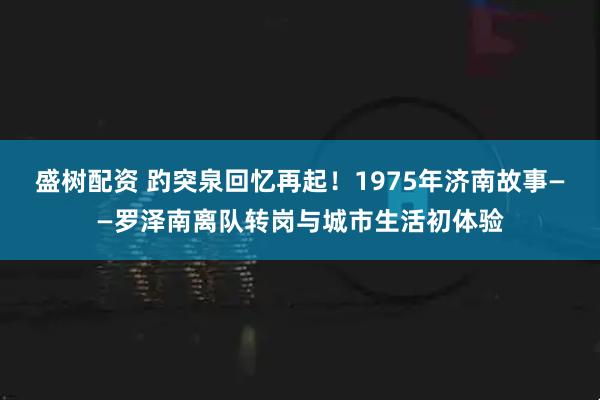
那年见过的泉水与柳影,像是在脑海里自己会开花。多年后回1975年夏天在济南的几步路、几段笑声,并不只是一次探友的旅程,它把一个年代的气质、几家人的家风、年轻兵的选择与去向,串成了清亮的一条线。到2009年秋,他已离那段岁月三十多年,再提起,仍能嗅到趵突泉边水气拂面的味道。
青年兵的岔路口:宣传队散、炮团合,与回地方的两条路
把时间扭回到1975年春,罗泽南从199师宣传队转往炮团。这在当时并不罕见:文艺骨干随着部队编制和任务调整,往往要在文艺、政工与技术兵种之间流动。宣传队承担的是演出、鼓动、政治教育,炮团则是技术性强、讲纪律与协同的硬仗单位。离开锣鼓与幕布,走向火炮与测算,既是岗位调整,也是身份转换。
展开剩余87%几乎在同一时段,他的战友马健、新民等人则办理了离队回地方的手续。两个方向,折射出当年青年兵的两种出路:继续在军中磨炼,或按政策回到城里参加工作。彼时“转业”“复员”与“回地方”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,背后还有一个“特招兵”的制度铺垫。罗泽南所在这批宜兴兵,就是通过“特招”进入部队的。早先带他们上路的是一位姓沈的副科长,办理入伍的环节,则借助了“在济南人武部长任上的小于父亲”这层关系——手续在济南完成,日后若要退伍回城,从路径上说,落在济南也是可操作的。制度之外的人情与渠道,构成当时青年兵流动的半隐形轨道。
简朴之家背后的分量:一个局长的客厅,一位“行政十级”的笑脸
夏天,他到济南小住,先去马健家。省商业局的家属楼安安静静,没有半点喧哗气派。屋里陈设简单:小桌小凳,片子床边是一张旧书桌,算得上体面的也只是那张用了许久的沙发。与“局长之家”的刻板印象不同,空出来的是清爽与节俭。马健的父亲在省商业局任局长,母亲在纺织厅是处级干部,都是能说上话的“领导”,但家里没有权势应有的腔调。
随后去中医学院看望新民。那套房子稍显书卷气,书比器物多。新民的父亲是老革命,资历深,行政十级。那一辈人的待客之道,不靠排场而在心气:老人笑容温和,自己端茶招呼,让两个年轻兵像回到亲戚家。行政级别在当时不仅对应工资,还对应名望与责任。“十级”在干部序列中颇有分量,常与厅局系统重要岗位相当。可真正让人记住的,反倒是那份不事张扬的稳重——“俭以养德”,古人话并不老。
两家对照着就显出一种气味:老革命出身的父辈把家过得干净俭朴,礼数足,分寸清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客厅里,年轻人有了“城里生活可以如此朴素而有温度”的直观印象。罗泽南那时不免感慨,若没有这类骨头硬、心地正的前辈,后来哪里来的江山与日子。他也隐隐担心:假如“个别权贵”的奢靡和贪腐成为常态,会不会漆黑掉最初的颜色。这份担心,很像一阵从泉水边吹来的风,清凉却让人心里有数。
一座城的温度:泉水、老巷与市场活力
走出家属楼,便是济南的水气。那时城里人车不多,天空很开阔。几人骑车去看泉,珍珠泉像一串串气泡从石缝里翻涌,趵突泉则像一口气直冲云天。垂柳轻垂在水面上,摇摇曳曳把阳光切成碎片。再往北是大明湖,风光铺陈开来,荷叶荷花简直像要溢到岸上。
更让人难忘的,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小商品市场。今天看未必能和后来涌现的商超相比,但在那个时代,货品比较全,服务也热情,人来人往,颇见“市”之活力。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松动的年代,活络的市场显出一种超前。省商业局的管理与引导,使这类市场成为城市经济温度计—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济南在商业活力上跑在了前头”的感受,会被来访的年轻兵牢牢记住。
摆脱手把的瞬间:骑车的笑与怕
要在这座城里自由穿行,得先学会骑车。罗泽南此前没怎么接触过自行车,马健便拉来两辆,说这样最省事。刚开始他握着车把,腰板绷直,眼睛往前盯,脚下用力却有些虚。马健在旁边扶着,说不急,脚下一蹬,车正人稳。练了几圈,终于能歪歪斜斜地往前走。拐弯和人多的时候还是会下车推着,谨慎得可爱。那年道路宽阔,车辆稀少,少年人的心跟着车轮一起滚,轻松而笃定。
约在东流水:集体放假的默契与一日之游
宣传队当时似有一回集体休假,留在济南的战友几乎都各自回家。大家约在“东流水王跟东家”集合——这个名字就像轻轻一拎,泉城的风味扑面而来。家家户户门前垂柳,巷子里处处有泉眼冒上来。离大明湖不远,水面上波光潋滟,荷风阵阵。王跟东的笛声在那一带也是记忆点,清亮悠长,像把水气吹得更远。
那天的目的地定在金牛公园。队伍里有马健、燕正、王跟东、小房、宿传军,还有罗泽南。几人骑着车一路唱着歌,公园宽敞,树影稀疏落在地上,阳光透过来,但不刺眼。大热天里,年轻人的兴致反倒被烘得更高,笑声比蝉鸣还响。这类同行,其实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“集体生活课”:不讲场面,大把时间拿来相与,感情在不经意处变得厚。
留还是走:来自一位母亲的邀请
在马健家的几天,一幕小小的插曲,折射了那时“落户城市、安排工作”的现实选择。吃饭间,马健的母亲很自然地对罗泽南说,日后如果退伍,不必再回去老家,可以到济南,她能帮忙安排工作,也能张罗对象,干脆把日子安在这里。话说得温和却有底气,这是一位在纺织厅担任处级职务的母亲,对一个年轻兵发自肺腑的照拂。对当事人来说,这不单是一句好意,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线——毕竟这批“特招兵”的入伍手续就是在济南办的,又有“人武部长小于父亲”的帮助,程序上并不难。
他当时也应承着,内心不可能不动。只是人究竟有根,故土与亲人常常是另一股拽人的力道。那一代兵的退伍安置,普遍在“个人意愿、组织安排、家庭牵挂、城市门槛”之间权衡。罗泽南后来的人生轨迹,证明他没有在济南落脚,但那次邀约与被关照的温暖,像一盏小灯,一直亮在心上。
制度的背影:干部级别、军队文艺与人武系统
把这些琐碎拼在一起,可以看到制度如何塑造个人的道路。其一,干部的行政级别,在当时与工资、待遇和岗位密切挂钩。“行政十级”不是空头衔,往往与厅局系统的关键岗位对应。其二,军队文艺宣传队承担着政治教育和文化慰藉,在和平年代具有凝聚士气的功能;而当编制收缩或任务变化时,人员调去技术兵种,是常见安排。其三,人武部是地方与军队之间的枢纽,征兵、转业、安置都绕不开它。像罗泽南这批“特招兵”,既有制度通道,也离不开具体干部的经办与兜底,这就是“沈副科长带队”“小于的父亲任济南人武部长”的意义所在。
个人的轨迹与后来的人生
离开军营之后,罗泽南并未选择单一的路径。他是1952年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位“多面手”:青年时下过乡,做过工,当过兵,后来经商,又走向艺术领域。在国有企业里,他长期从事管理工作,1993年起转向紫砂壶艺的创新与制作,作品多次在全国美展中获得银奖、铜奖。今天他定居上海,把手艺做得静气十足,心里珍藏的,仍然是那个夏天的泉水和朋友们的笑。
如果把这些串联起来那年在济南的几次出门,并不只是游玩。珍珠泉的水泡、趵突泉的喷涌、金牛公园的林荫、邮电新村和中医学院里那股书卷气,再加上小商品市场的热络,都构成了一个“未来可能”的样子:更开放的城市,更有活力的商业,更朴素却有力量的家风。这样的环境,给后来一个做艺术的人以审美的濡染,给一个从制度里走出来的人以尺度与分寸。
记忆的回声与一代人的品格
时间过去了三十四年,写下回忆的时候是2009年9月23日。他把那段岁月浓缩成四句感怀:年少时的无忧、四处游荡的自在、战友情谊的深厚,以及不愿遗忘的执拗。这四层意思,既是个人的,也是那代兵的集体画像。“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”,水向东逝,记忆却逆流而上。马健父母的体面与简朴、新民父亲的慈和与分量、燕正与王跟东的热情、还有小房和宿传军在烈日里骑行的背影,都在记忆的湖面上留下波纹。
在这些人和事之间,还能读到更深的一条线索:老一辈革命者留下的家风——朴、直、严、一以贯之——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传给了年轻人;军旅之中的纪律、集体、荣誉,如何在离开军营后仍然塑形;而城市的泉水与市场,如何预示着一个社会正在从单一走向多元。罗泽南把这条线握得很松,不做夸张的,却在不经意中留给读者一种明白:真正的重量,常常躲在平常处。
再回想起“东流水王跟东家”那次集合,满城是柳影与泉声,远处是湖上的风荷。那个下午,笛声顺着水意慢慢行走,仿佛把人心里的一些轻和重都吹散了。这就是记忆的好处:它不为我们修改事实,却会在长久的发酵后,把情感蒸馏得更清澈。说来简单,不过是骑车、看泉、串门;说来不易,是一代人从军营走向城市,从集体走向自我,同时努力把“俭以养德”的老规矩留在心里。如此,泉水不必永喷,柳条也会换新,但那年的夏风,总会在想起朋友名字的时候,又吹过来。
发布于:江西省宝龙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